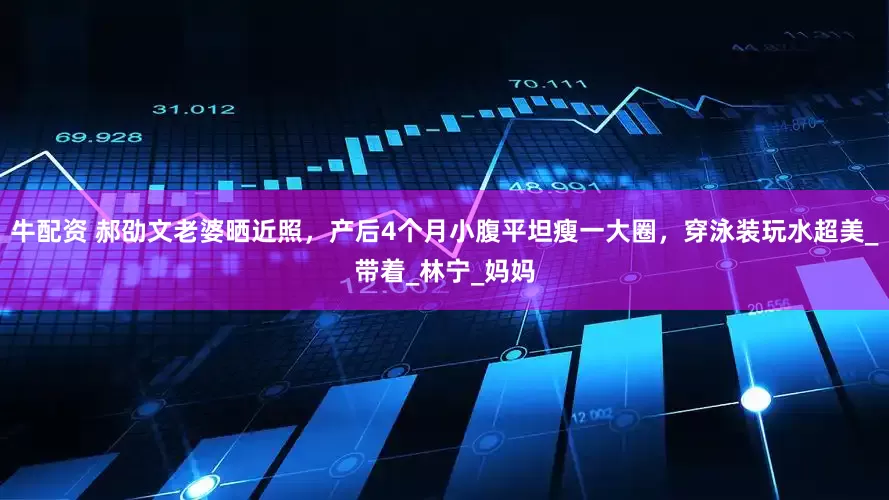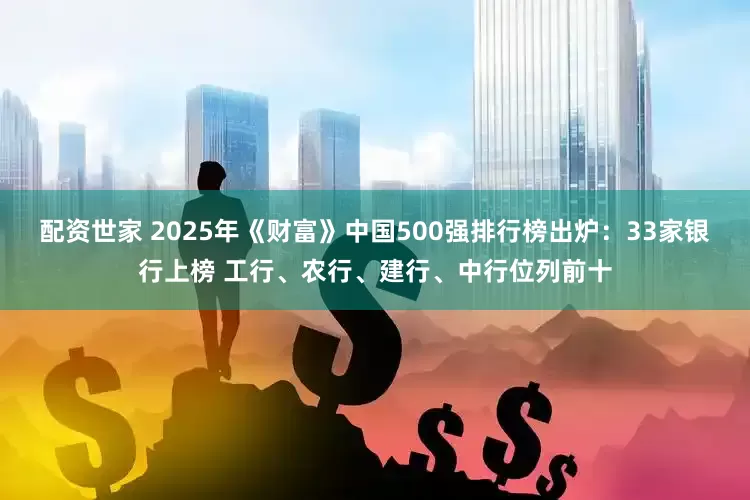残阳把天际染成凝血般的红,李大福背着那柄拖到脚踝的长刀,一步步踩碎满地金红的余晖,停在铁匠铺前。
铁匠刚把最后一块马蹄铁扔进冷水桶,抬眼就看见了那刀。
那刀是双手柄,刃身足有一米二,宽厚如古砖,刀尖斜挑着像头蓄势的狼。只是此刻刃口卷得像枯荷叶,满身的豁口倒像是刻着二十年来的风霜 —— 四斤八两的分量,铁匠闭着眼都能掂出来。二十年前他亲手锻的刀,刀柄缠着的鲨鱼皮都磨成了深褐色,唯有那 "刀王" 二字的烙印还在,只是被血渍糊得快要看不清了。
"老刀王......" 铁匠喉结滚了滚,没再说下去。他懂这行的规矩:刀在人在,刀回炉,便是人已亡。
为刀王铸刀,是铁匠家传的宿命。师父当年为老刀王铸完刀,咳着血倒在淬火池边;他十年前为李大福师父铸这刀时,还笑着说 "够你耍到白头",谁料这刀的主人竟在壮年倒在鬼子的刺刀下。铁匠捏了捏掌心的老茧,炉子里的火 "噼啪" 跳了一下,映着他眼里的光 —— 这炉要重开,不只为了新刀,更为了老刀王没杀完的鬼子。
展开剩余73%残阳彻底沉下去时,铁匠接过旧刀。三炷香在风里抖了抖,烟直直地飘向西南 —— 老刀王牺牲的方向。祭刀的酒洒在刀身上,顺着卷刃的豁口渗进去,像是在舔舐旧伤。炉膛里的火 "轰" 地窜起来,酱紫色的火苗舔着炉壁,把铁匠的脸烤成紫铜,汗珠刚冒出来就被烤成白汽。
墙角的大茶壶咕嘟着,铁匠抓把粗茶扔进去,沸水翻涌时,茶叶浮上来又沉下去,像极了山下那些挣扎的百姓。他盯着炉膛里的铁,看那暗红渐渐变成亮白,突然抄起铁钳,"哐当" 一声把烧透的铁坯按在铁砧上。铁锤落下去的瞬间,他吼了声什么泸深通,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。
豆大的汗珠砸在铁砧上,溅起细小的白汽。铁匠的腱子肉在火光里绷得像铁块,古铜色的皮肤下青筋突突跳着,那张被炉火和岁月凿出棱角的脸,倒像是用同一块铁锻出来的。他抡锤的节奏越来越密,"叮咣、叮咣" 的声响撞在山壁上,倒像是在给死去的冤魂敲丧钟。
李大福站在三步外,眼睛一眨不眨。他看着那柄陪了师父二十年的刀被扔进炉膛,看着它在火里渐渐变成一条通红的蛇,看着铁匠的锤子把卷刃敲平,把豁口补上 —— 每一次敲打,都像是在捶他心里的恨。
他想起前天在紫云山下,自己正握着木刀跟师父练 "拦腰刀",山坳里突然滚来鬼子的皮鞋声。那些戴钢盔的影子把逃难的百姓圈成圈,机枪扫过,哭喊像被掐断的弦。师父把他塞进山洞时,掌心的老茧蹭得他脸生疼:"待着,活下来。"
等他扒开乱石冲出来,西山的土坑里已经堆起了半人高的尸体。师父浑身是血,手里的刀断成两截,却还死死咬着一个鬼子的耳朵。看见他,师父吊着最后一口气,让他练“破锋法”。
"迎面大劈破锋刀,掉手横挥使拦腰......" 他挥着木刀哭,师父却瞪着眼纠正:"刀尖朝下,刃朝自己...... 格开步枪,顺势斜砍...... 这才是杀鬼子的招!"
"把我埋在三道沟,带刀去找城北铁匠...... 投奔皮司令...... 就说小亮子让你去的......" 师父的手垂下去时,指缝里还攥着半块被血浸透的刀谱。
炉火 "腾" 地窜高半尺,把李大福的脸烤得发烫。他抓起铁匠那只结着厚厚茶垢的水壶,猛灌了一大口。苦涩的茶水滑过喉咙,倒像是把喉咙里的火浇得更旺。手一抖,水洒在铁砧上,"滋啦" 一声腾起白雾。铁匠突然一脚踢向铁砧,那几百斤的铁块 "哐当" 翻了个身,他铜色的脸上竟泛出金红的光 —— 一柄黝黑的长刀躺在砧上,刃口亮得能照见人影。
李大福掂刀时,指腹触到刀柄上新缠的鲨鱼皮,糙得正好发力。他走到铺前的空地上,夜风吹起他的衣角,刀身在月光下划出一道冷弧。先练无极刀法,沉缓如老松;再换破锋刀法,迅猛如惊雷。没有半分花哨,每一刀都奔着 "断颈"" 破腹 " 去,八个招式十六个动作,在草地上刻出深深的刀痕,倒像是把满腔的仇怨都刻进了泥土里。
刀风 "呜呜" 地啸,惊得远处的狗吠了几声,又很快噤声。
天快亮时,李大福收刀入鞘。铁匠站在门口,往他包里塞了三个窝头:"皮司令在西北,一路保重!"
他没回头,只是挥了挥手,背着新刀走进晨雾里。那刀在鞘里轻轻震,像是在应和着什么。
后来,据豫西抗日革命纪念馆藏的《汝河抗战实录》记载:民国三十一年,汝河县村民李大福投身西北军大刀队,在郏县遭遇战中,以一把重铸的大刀与日军近身肉搏,斩杀五十四人。那刀上的血锈后来磨成了红砂,而他 "豫西抗战第一刀" 的名号,至今仍在嵩岳山间回荡。
发布于:河南省长宏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